一八五三年,在德国西南部小城欧芬堡,亚尔萨斯雕刻家弗里德里希于市中心的大理石基座上立起一尊德雷克国士的雕像。弗里德里希以传统遥望远方的姿态,来表现德雷克凝视地平线的神态。他的左手放在剑柄上,右手握着一颗马铃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基座上面写着:
将马铃薯带到欧洲的传播者。
在土地上努力耕和的数百万农民,
不会忘记他的恩德。
这座雕像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被纳粹拉倒,这场小规模的暴力骚乱事件又称为水晶之夜。摧毁这座雕像是一桩破坏艺术的罪行,而非破坏历史: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德雷克并未将马铃薯引进到欧洲。就算他「曾经」引进马铃薯,这座雕像也有误导之嫌。欧洲人能够栽种马铃薯,绝大多数都该归功于驯化马铃薯的安地斯居民。
从地理来看,安地斯山脉不太可能是种植主要粮食的地方。这座地球第二大的山脉,连绵的山峰构成南美洲太平洋岸的冰冻屏障,全长达五千五百英里,许多地方高度也超过了两万两千英尺。活火山散布在山脉沿在线,就像钻在腰带上的熔化宝石。上个世纪,光是厄瓜多就有七次火山喷发,位于智利东部边境的圣荷西火山」从一八二二年以来喷发了七次。这些火山连结着地质断层,两相推挤之下引发了地震、洪水与山崩。即使在地震较少的时期,气候的变化也相当活跃。高地的气温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内从华氏七十五度(编按:摄氏二十四度)陡降到冰点以下,因为空气太稀薄,无法产生保温的效果。突如其来的雹暴往往能撃碎车窗,引发一连串交通事故。著名的圣要现象(这个名字是安地斯居民所创)为沿岸带来洪水,为高地平原带来旱灾。圣婴现象可以维持数年之久。
安地斯山脉的主要部分由三个约略平行的山脉链组成,这三个山脉以高原相区隔,而这些高原统称为阿尔蒂普拉诺高原。阿尔蒂普拉诺(平均高度约一万两千英尺)是安地斯山脉最主要的可耕地区,这就好像欧洲仰赖阿尔卑斯山脉的农地存活一样。安地斯山脉的东面有来自亚马逊流域湿热的水气在此成云致雨,西边面海的一面由于受到山峰「雨影」效应的影响,使这里成为地球上最干燥的区域。介于两者之间的阿尔蒂普拉诺干湿分明,绝大多数的雨水出现在十一月到三月之间,而这里也自然形成平坦的大草原地带。
然而,这个看似毫无前景的地区,却发展出令人晌目的伟大文化传统I佛蒙特大学地理学家盖德巳认为,这个文化在一四九二年时已达到世界上所有山地文化的「巅峰水平」。正当埃及王国建立金字塔时,安地斯社会也正兴建他们自己的纪念性神庙与仪式广场。从厄瓜多到智利北部,各个小国不断争夺着统治权。纳斯卡以其石头线条与动物图案闻名于世;査文的雄伟神厕位于査文德万塔尔牙;瓦里盛产优秀的地貌工程师;莫切享理四海的陶器描绘了生活的各种面向,包括战争、工作、睡觉与性;蒂瓦讷库是该区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文明(以的的喀喀湖〕为中心,这是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可航行湖泊;奇穆尔是莫切的后继者,首都昌昌不断往外扩展,城市人口极为可观。今日最著名的是印加,它透过征战兼并了泰半的安地斯地区,建造绵密的道路网与富丽堂皇的黄金城,最后败给了西班牙的疾病与士兵。
中东与埃及的文明史,与小麦和大麦的发展密不可分;同样地,墨西哥与中美的原住民社会则建立在玉米上。在亚洲,中国形诸于文字的历史则受到米的影响。安地斯地区与上述地区不太一样,当地的文化不是由谷物滋养,而是来自于块茎与块根植物,其中马铃薯是最重要的。
考古学家于智利南部发现一万三千年前人类食用马铃薯的证据,不是现代的马铃薯,而是仍生长在沿岸地区的野生种。不过,遗传学家还无法确定安地斯文化驯化马铃薯的确切过程,因为早期的安地斯原住民主要是由种子来种出块茎,而且显然在同一片菜园里种了不同品种的马铃薯,因此产生出无数天然的混合种,其中一些种类可能产生出现代种的马铃薯。一份经常受到引用的分析试图厘清这段过程;在经过大量研究之后,该分析报告的作者表示,今日的马铃薯来源有四种,其中两种「未知」。至于何时岀现,也不得而知:考古学家只确定一件事,安地斯居民在公元前二000年时已经可以吃到驯化的马铃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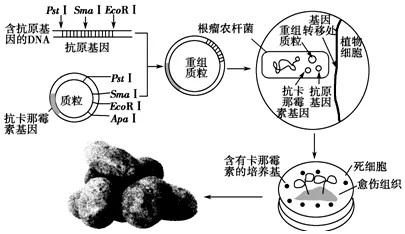
马铃薯显然不是个容易驯化的植物。野生块茎含有茄碱与西红柿碱,这些有毒的化合物可以让植物免于遭受危险有机体如真菌、细菌与人类的侵扰。烹煮通常可以破坏植物的化学防卫机制I举例来说,许多豆类植物在经过浸泡加热之后就可以食用——但茄验与西红柿验却不受这些锅炉影响。安地斯居民然是藉由吃土 (精确地说是结土)来中和毒素。在阿尔蒂普拉诺高原,原鸵与小羊鸵,大羊鸵的野生亲戚)在食用有毒的植物之前会先舔食黏土。叶子里的毒素会附着——更技术性的说法是「吸收」在细微的黏土粒子上。毒素与土结合,这些有害的物质就能通过动物的消化系统而不会影响动物的健康。印第安人仿照这段过程,把野生马铃薯浸泡在黏土与水混合的「减汁」里。最后,他们培育出毒性较低的品种,不过有些古老而毒性较强的块茎依然存在,这类品种往往较能抵挡寒冻,因此还有留存的价值。现在山地市集里仍有人贩卖成袋的黏土,放在餐桌上佐马铃薯吃。